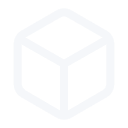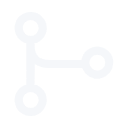南洋老屋的一碗潮汕猪杂汤粉
雅加达老城区的热风裹挟着香料与海腥的气味,柏油路面被上午的烈日烤出摇曳的波纹。我避开推销水果奶茶的商贩,带着同伴A钻进一栋薄荷绿窗棂的荷兰老屋。
这老屋离我入住的酒店不过几步路,实在不是一个远道中国深圳来的外贸人最佳猎奇选择,我第一次来印尼的同伴A拉拉我的衣袖,意思是能不能再走两步路,看看有没有当地更好玩更好吃的餐厅。我笑着妥协道先进去看看。心里已经盘算好,我们入住的是印尼雅加达穆斯林老城区,这方圆10公里之内断然找不到能符合中国胃的美食,而这家厨房外露的布局显然表明是个种餐馆,即使门口冷清,门楣上招牌已褪成浅金也看不出这家店到底是卖什么的,但就像我这样吃不惯叁巴酱的异乡人,总要寻着这沾着中国胃的故乡美食,卖什么不重要,中餐就行。

八十岁的媚姨正用印尼语招呼唯一的客户- 我和A进来,见到我们时又立即切换成带着南洋腔调的普通话:“阿妹,从中国来捏?”她梳着整齐的发髻,真丝衬衫纽扣是两枚温润的南洋珠,行动时腕间老坑翡翠发出轻响。我顿时对她和这家餐馆充满兴趣。
我是赣北皖南人,和同是赣籍人士A拥有同一种胃,然而我又比她特殊点,因为非常认同广东文化让我又拥有广东胃,在深圳扎根数十年时间的我早已尝遍各种广东美食,品鉴潮闽客粤各大名菜,而看这桌子上菜单一点也不陌生,这是经典的潮汕猪肉杂汤粉,做法一模一样,连汤粉灵魂炸蒜头碎都保留了。

我跟A 细致的介绍这道菜的来历以及历史渊源,A瞬间就有了胃口,于是我们落座了。
汤粉端上来时,A大块朵颐,大呼好吃,我则暗笑。老板奶奶忍不住坐在我们对面就这样开始唠起来,她的名字和她本人一样美。“三十五岁那年,他出海遇了风浪。”竹筷在她指尖轻点桌面,“两个囡仔要吃饭,我就拎着珠宝箱满世界跑。”她的目光穿过缕空雕花窗,仿佛能望见1983年飞往慕尼黑的航班。那时她带着苏门答腊的猫眼石,在德国商会的冷餐会上周旋,用计算宝石克拉的天平称量人心。
一碗汤粉早就已经被我们嗦得汤都不剩,两双筷子散在桌子上,我们撑着脑袋好像在听自己家的祖母讲年轻的事情,浑然不觉天已经全部黑了。
老屋深处俨然是座微型博物馆。波罗洲的沉香木佛雕旁挂着瑞士八音盒,荷兰锡器与景德镇青花瓷在博古架上对话。她抚过一只鎏金怀表:“雅加达的生意人分三种——椰子树一样扎根的华商,随季风来往的阿拉伯人,还有藤蔓般依附权力的掮客。”突然指向窗外飞驰的奔驰车,“那家的祖父在我这里赊过米粉,现在子孙开锡矿,但是十几年没有联系了。”

四周店铺都熄灯打烊时她送我们至巷口,一盏暖灯着殖民时期建筑群的拱廊。“这栋老屋是拿第一桶金买下的。”她指了指房子的天花板,“每年税费很贵啊,这个数”她伸出4个手指,我立刻盘算一下她店里的现金流,按照这个现金流应该是亏的,媚奶奶又突然压低声音:“斜角那家五金店,女儿去年嫁给了泗水糖王的后人——你明日若去跟华人谈生意,不妨带盒潮州茶饼。这一带都是潮州人。”
我想我的担心是多余的。
我们走回酒店了,回头望去,媚奶奶正在擦拭我们刚吃过的桌子,又来了一家6口食客,媚奶驼着背登时异常忙碌,她的身影与满室收藏品渐渐融成温暖的剪影。忽然明白她展示的不是奇珍异宝,而是用八十载光阴凝练的生存智慧。当年肩扛珠宝走四方的单亲母亲,与此刻守护着汤粉锅的老厨娘,始终是同一个灵魂——既能在世界地图上标记航迹,也懂得在香料群岛守护最本真的滋味。

离开昏暗的柏油路,街道上是印尼特殊的水果香草味,有点燥热,有点清香。我攥着写满商贾关系的纸巾,忽然懂得真正的外贸从来不只是货品流通。当媚姨用福建话念出“汝食未”时,当潮汕鱼丸在南洋椰风里翻滚时,那些被揣在行囊里远渡重洋的,何尝不是一个个民族生生不息的根脉?这位用珠光宝气点亮人生,又最终回归市井烟火的女性,早已在时代浪潮中将自己打磨成最璀璨的收藏——既见证过世界之大,也守护着方寸之深。
明年,我一定要找个不是出差的日子,再次见一见这位美丽的老奶奶,再点上一碗潮汕猪杂汤粉。(插图为当时店内实拍)